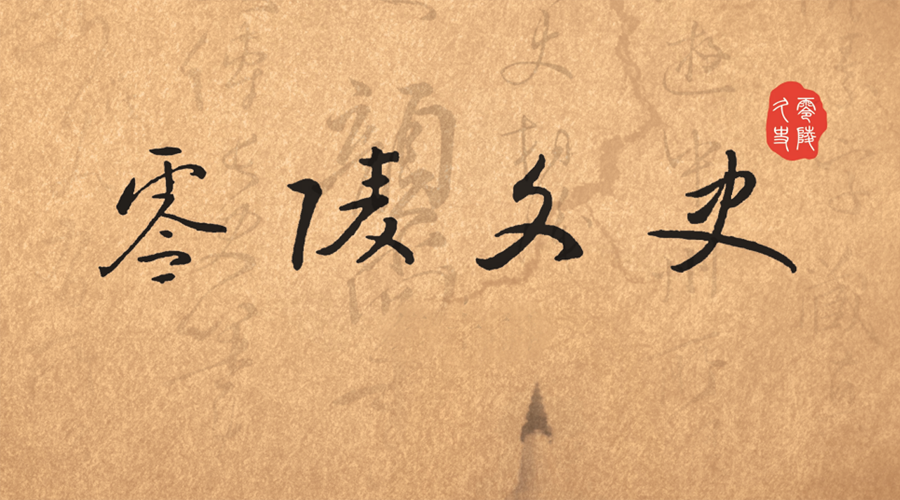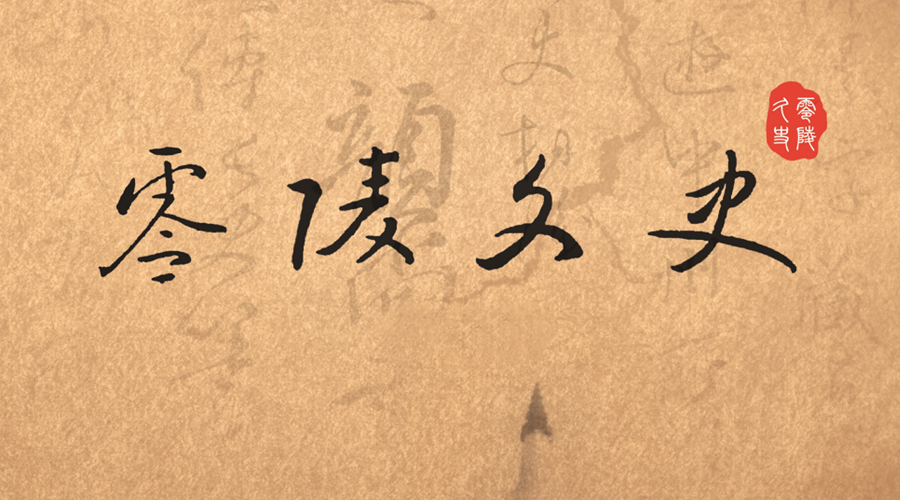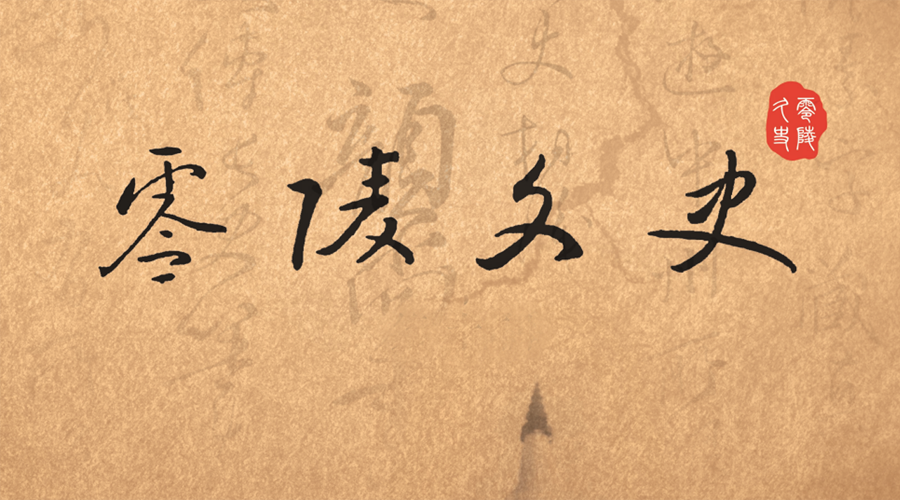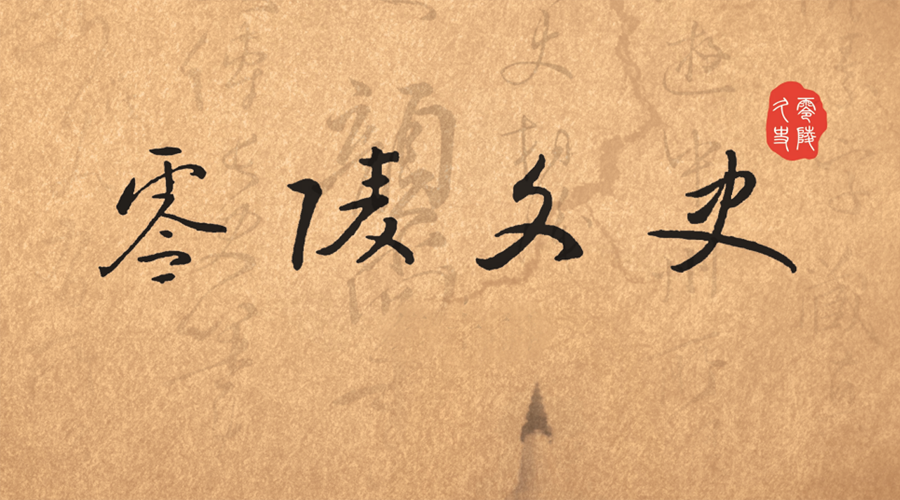零陵文史|潇湘与三湘
潇湘与三湘,常常是湖南的代称。其实,这两个名称是永州零陵对湖南的文化贡献。
先说潇湘,她是两条汇聚的河流。潇是永州市域的潇水,湘发源于广西,自南部永州经衡阳、株洲、湘潭、长沙、岳阳,贯穿湖南南北注入长江的大河,全称湘江。她是湖南省代表性的江河,湘自然成了湖南的简称。潇水是湘江上游最重要的支流,与湘江在今零陵城区的蘋洲交汇,是为潇湘。
潇湘一词最早见之于《山海经》,这是先秦传至汉代成书的重要典籍。《山海经·中山经卷五》:“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浦。”这里所说的“帝之二女”,即舜帝与其两位妃子娥皇、女英的故事。根据司马迁《史记》: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帝崩葬藏精于九疑山,零陵得名亦与舜帝有关。娥皇与女英两位妃子,从北方前来寻夫不得后,投水溺亡,谱写出千古第一爱情绝唱,潇湘成为历代文人咏叹的对象。南朝谢朓:“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送范云出任零陵内史》)。唐代李白:“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远别离》)。柳宗元:“九疑浚倾奔,临源委萦回。会合属空旷,泓澄停风雷”(《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刘禹锡:“楚客听罢瑶瑟怨,潇湘深月夜明时”(《潇湘神》)。宋代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偶读旧稿有感》)。元代耶律楚材:“凤池分付夔龙去,万顷潇湘属湛然”(《用薛正之韵》)。明代徐祯卿:“帝子葬何处,潇湘云正深”(《古意》)。唐瑶:“归来晚渡潇湘水,应有潜蛟避使旌”(《朝阳岩听泉亭》)。曹学佺:“潇水入湘终古碧,零陵生草至今香”(《潇湘》)。清代李明秀:“碧波潇湘映朝晖,水泛濒洲接翠微”(《湘口待友》)。阮元:“零陵城边黄叶渡,柳侯祠前多竹树。布帆无恙挂西风,正是潇湘合流处”(《过潇湘合流处》)。
《山海经》一书并非成于一时一人,潇湘一词出现的时间应该肇始于先秦,至汉以后广为流传,不断被赋予新内容,成为美的象征。
潇水与湘江在零陵蘋洲相汇,有如一对倾心相恋的爱人,将蘋洲紧紧地拥抱在怀中,成为潇湘源头一帧感天动地的画面。
潇与湘分别为声韵萧、相部,复合后成为声母同部的双声叠词,读起来朗朗上口,好听又耐用。潇湘被用作词牌《潇湘神》,琴曲《潇湘水云》,戏码《潇湘夜雨》,画题《潇湘八景》,小说《红楼梦》第一女主林黛玉居所“潇湘馆”等。它还被衍化为地域名称,唐代杜甫:“五载客蜀鄙,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去蜀》)。宋代张孝祥:“归辅五云丹陛,回首楚楼千里,遗爱满潇湘”(《水调歌头·送刘恭父趋朝》)。明代何景明:“长风度关塞,九月下潇湘”(《雁》)。诗人们在这里所言潇湘,即泛指今湖南省,约定俗成,逐渐为人们接受并使用。
再说三湘,自宋以来,用“三湘”代指湖南,然而,“三湘”实指本源为何?则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所谓地名的合称,这是最早见于宋代《太平寰宇记》的说法,认为湘潭、湘乡、湘阴三县合称“三湘”。第二种是水名的合称。这方面又有两个版本。清代光绪《湖南通志》记载:“湘犹相也,言有所合。至永州与潇水合,曰潇湘;至衡阳与烝水合,曰烝湘;至沅江与沅水合,曰沅湘。”这个版本提出潇湘、烝湘、沅湘为三湘。还有一个版本认为是潇湘、资湘、沅湘,也就是把湘、资、沅三水合起来称为三湘。
其实,这些说法的所谓三湘都不正确。
前一种关于湘潭、湘乡、湘阴三个地名合称的说法,没有传递任何新的地名意义。因为,它表达的只不过是一种名称上的耦合,说明三个地名前面都冠之以湘而已,绝对不可能用来指代湖南。
后一种关于水的合称的说法,两个版本都不准确。从讲潇湘、烝湘、沅湘这个版本来看,讲湘江流到永州接纳了潇水,流到衡阳接纳了烝水,这是对的;但是流到沅江接纳了沅水,这就错了。因为,湘江到湘阴县已经流入了洞庭湖,怎么可能还到沅江去接纳沅水呢?即便今天的沅江市地处南洞庭湖,也就是在洞庭湖中部的位置,按照沅江人很夸张的说法,这里“汇集湘、资、沅、澧四水”,那也是对洞庭湖接纳四水的描绘,而不是湘水进入洞庭湖以后再去接纳沅水。再者,从陆地上看,湘水与沅水之间还隔了一条资水,这样两个不同的水系不可能有在地面上串联的关系,所以,光绪《湖南通志》的沅湘说法是不存在的,包括使用“合”的语言文字,也都犯了常识性的逻辑错误。至于讲把湘、资、沅三水合起来称为三湘的版本,更是毫无道理的拉郎配。因为,潇湘本身属于湘江,讲湘可以理解,而资湘、沅湘则是硬生生地把资水、沅水与湘水扭在了一起。产生这种误导的根源,主要是只想将三湘这个响亮的名称拿来为我所用,漠视了古零陵郡三湘形成的地域内涵,以至于用现时的行政区域去解读而越说越乱。无独有偶,清代魏源在《三湘棹歌》序中曾说:“楚水入洞庭者三:曰蒸湘,曰资湘,曰沅湘,故有三湘之名。”这里且不说拉扯资湘、沅湘的错误,特别突出蒸(烝)湘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烝水与耒水差不多在同样的地点同时注入了湘江,但以对湘江的贡献来说,烝水比耒水要小得多。烝水源自今天的邵东,仅流经衡阳县和衡阳市区,全长约200公里;而耒水发源于今天的郴州桂东县,流经资兴市、永兴县、耒阳市、衡南县,在衡阳市区的耒河口汇入湘江,全长453公里,是湘江最长的支流。按照河流长度、流域面积以及河道产水量,排列支流与湘江的关系,耒水远远地排在烝水的前面,但为何没有产生耒湘却出现了烝湘的说法呢?
三湘的本源就是古零陵郡,即漓湘、潇湘、烝湘都在零陵郡范围。零陵郡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汉武帝设置零陵郡辖有十个县及侯国,其郡治零陵县在今广西全州县与兴安县交界的地方。根据谭其骧先生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西汉零陵郡的十个县及侯国是这样分布的,当时的零陵县南边为始安县,也就是今天的桂林市;北边有洮阳县,主要是今天的全州县;营道县在今天的宁远与道县之间;营浦县在今天的道县西、双牌县南、江永县;冷道县在今天的宁远县东;泉陵侯国即今天的零陵区、冷水滩区、东安县、双牌县北、祁阳县、祁东县;钟武县在今衡阳县;都梁侯国在今天的武冈、洞口、绥宁、城步;夫夷侯国在今邵阳西。也就是说,西汉零陵郡的范围,覆盖到了今天的广西桂林市,湖南邵阳市以及衡阳市的一部分。东汉时期,零陵郡治迁至泉陵侯国,辖地新增了湘乡县和昭阳侯国、烝阳侯国,扩大到今天的娄底、湘乡、双峰、邵东等地。烝水发源于今天的邵东最高峰大云山脚下,经过佘田桥南拐到衡阳县金兰镇,在衡阳市烝湘区注入湘江,成为所谓的烝湘。这样,汉代零陵郡以湘水为主干,演绎出漓湘、潇湘、烝湘的三湘故事。
“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这句话出自《水经注》,也是对湘江源头最早的文献记载。《水经注》中还写到:“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关于漓湘的最早记载。考察古零陵郡的行政版图,湘江上游的源头上有漓湘,当时的零陵县、始安县、洮阳县在漓湘一片;一路下来有接纳潇水的潇湘,营道县、营浦县、冷道县、泉陵侯国在潇湘一片;再下来到接纳烝水的地方就有了烝湘,都梁侯国、夫夷侯国、昭阳侯国、烝阳侯国、重安县(原钟武县)等,都在烝湘一片。从汉武帝置零陵郡的公元前111年到东汉(25—220年)的三百余年间,零陵郡幅员涵盖了漓湘、潇湘和烝湘的广大地域。三湘成为零陵郡的代名词,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也是汉唐之际三湘这个词语面世的历史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有的行政区都分解划小,汉代大致的湖南范围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变为八九个郡。准确的说,三国时期零陵郡的北部新设了湘东郡,郡治在酃县(今天的衡阳市);衡阳郡,郡治在湘南县(今天的湘潭市)。西晋时期,零陵郡的南边划出了始安郡,郡治在始安县(今天的桂林市);北部新设了邵陵郡,郡治在邵陵县(今天的邵阳市)。而当时的长沙郡只相当于今天的长沙东部和岳阳,域地也大大的缩减,郡治临湘县也就是今天的长沙市。尽管当时有了这样的调整变化,不少人仍然沿用古零陵郡三湘的说法。郦道元是西晋以后的北魏人,他的《水经注》仍然说“湘水出零陵始安县”,将漓湘之地的始安县仍然看做零陵郡的范围。唐代诗人李白《悲清秋赋》中有“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这里的登九疑、见三湘,讲的就是古零陵郡的范围。唐代潭州刺史张谓《长沙风土碑铭》中的“五岭南指,三湘北流”,也沿袭了汉代零陵郡三湘的说法。唐代以后,漓湘之地的桂林不在湖南观察使的地域范围,而逐渐淡出了湘人的文化视野。明清时代,湖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并简称为“湘”的时候,三湘的含义已经模糊不清,则开始被借用为湖南的代称,还将湘、资、沅、澧四水与三湘连接起来,统称为三湘四水,这是在地名的历史传承与现实融合中的解读,即使有了对古代三湘的现实误读,也并不妨碍人们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魏源是邵阳人,更是近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家乡不仅有蒸水、资水,而且与沅水相邻,所以他在解释楚水入洞庭湖时,将烝、资、沅三水都与湘粘连在一起来演绎,这主要在于他对家乡的偏爱所致,实质上造成了对三湘读解的误导。
漓湘、潇湘、烝湘所共同形成的三湘,是古零陵郡的文化创造。正如今天我们用“潇湘”作为湖南的代称,湖南卫视使用“锦绣潇湘,快乐湖南”宣传广告语一样,“三湘”与“潇湘”,都是零陵历史文化对湖南奉献的两个美好名称。
作者:蔡自新 编辑:王先均


 标准
标准



 A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