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在文学中与洞庭湖风雨同行
人物名片:沈念,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三毛散文奖等
沈念:在文学中与洞庭湖风雨同行

2022年11月20日晚,“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举行。现场文学星光璀璨,43岁的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沈念凭《大湖消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被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的沈念,近年来佳作频出,曾获得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高晓声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2021年,他为家乡洞庭湖写下一部田野志《大湖消息》,字里行间满怀对故乡的深情与眷恋、忧思与憧憬。
“作家是时间里的人,也是改变时间的人。”沈念说,“作家在时代里生活,也在创造这一时代的文学记忆,要写出岁月不居中的真善美,写出值得钦佩的道德勇气,写出可以信任的希望和灵魂。”
年少成名,从记者转型作家
穿着黑色皮衣的沈念冷静内敛,有些像他笔下的洞庭湖,乍看之下有种疏离,随性起来又释放出一种少年感。他的家乡华容县位于洞庭湖和长江交集之处,和《大湖消息》里的众多人物一样,他也是一名地道的“江湖儿女”。

沈念曾在洞庭湖边一所纺织厂子弟学校工作了十年,教语文,创办了文学社和后来很多学生都记得的校园刊物《太阳雨》。21世纪初的大型国企,文化氛围浓厚,单身青年宿舍住着许多文艺青年,青春的萌动,情感的迷茫,让年轻的沈念一头扎进文学里,逐渐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
2004年,《芙蓉》杂志为了挖掘湖南新生作家,从当时湖南众多“70后”作家中挑出五位各有所长的佼佼者,开设了“新湘军五少将”专栏,25岁的沈念便是其中之一,他顿时成为备受瞩目的湖南文坛新星。
时任《岳阳晚报》领导惜才,将沈念调进报社。从学校到党报,沈念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空间。但他未能如愿进入副刊部,而是很快便被看中负责市里主要领导的时政报道。
“我最初对时政报道有点排斥。”一开始沈念没摸清时政新闻的模式,第一篇稿子是领导秘书逐字逐句改出来的。很快他适应了时政报道风格,找到了技巧,往往会议刚结束,他的稿件就已经写完送审且深得好评,他成为岳阳市新闻界有名的“快枪手”。
八年后,沈念已经担任了三任市委书记的随行记者,看上去忙碌而风光,但对年复一年似曾相识的活动,他开始感到重复和枯燥,并为没有时间进行文学创作而焦虑。意外的机会之下,2014年他调到省作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远离了过去的热闹,意味着大部分时候要很孤独很寂寞地去创作。”沈念说,“当时没想过将来要走多远,但是不去走,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
《大湖消息》凝聚多年生命经验
迁居长沙后,沈念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洞庭湖是自己生命中最有力量、最富情感、最具意义的一块福地。无论他离开那个大湖有多远,“睁眼闭眼就能看到它的波澜,听到它的涛声,闻到它的呼吸”。
他担心自己失去和洞庭湖的紧密联系,这些年来没有中断过回到湖的身旁。在很多年的元旦前后,他都跟着东洞庭湖越冬水鸟调查组,扎实地深入湖区走几天。那些年正值洞庭湖湿地保护及渔业的转型时期,也是矛盾最集中的阶段,“那些直接尖锐的矛盾、生态的纠结,以及它们给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带来的困扰,给我留下了直观而深刻的印象。”
2020年下半年开始,沈念又数次深入洞庭湖,在渔民家中借住,在冬天空旷无人的湖上坐船夜宿,见到了与过去认知中不一样的湖,也激活了生命中那些和洞庭湖相关的经历。

沈念(中)采访麋鹿饲养员。
在《大湖消息》中,上篇“所有水的到访”写湖区动植物的变迁史,下篇“唯水可以讲述”写湖区人的命运史。正如沈念所说,这本书“记录的是田野经验,抒怀的是生命史,通向的是人心”。
鸟类的往返、江豚的悲歌、麋鹿的消失与再生、黑杨的“兴亡”,一个个故事引发读者思考“人类和自然应该如何和谐共生”;生存各异的渔民、胸怀壮志的保护区工作者、天南海北的过客,令人对“江湖儿女”的命运心生感叹。
“只要人停止杀戮动物,给它们自由安定的空间,它们很快会忘记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血腥经历,而与人重归和睦。”因为和一只白鹤的缘分,红旗湖的老鹿从一位打鸟队长转变为远近闻名的护鸟人,并得出了对人与自然相处的答案。这与其说是老鹿的体会,不如说是沈念的期待。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来,退田还湖、生态修复、十年禁渔、守护好一湖碧水成了湖区人的自觉与自省。
“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永远会有新的矛盾和问题在不断碰撞、撕裂和开拓,任何时候都不要去否定这样的矛盾。”在沈念看来,文学作品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但它可以为解决问题提供文学样本和文学途径。”
未来用小说为洞庭湖立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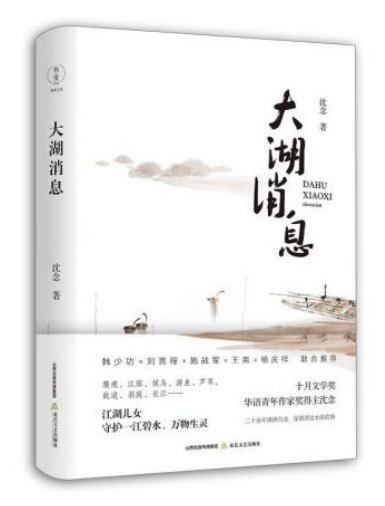
《大湖消息》出版后,很快登上各大新书榜,获得鲁迅文学奖,最近已再版第四次印刷,这些并不在沈念的预期之中,也没有让他特别兴奋,但在他心里多了创作上的自信和严苛。
他笑着回忆,母亲以前对他最大的期待,是成为学校的总务主任,“她觉得不用每天很辛苦地上课,而且似乎比较实惠。”
“我感觉湖区的人不会想着怎么去积累财富,他们特别讲究随着水流走,衣食方面无忧就过得很惬意,就喝酒,不会去盖房子,大手大脚把钱吃完喝完,这和过去无法建房、经常有水灾有关。”这是《大湖消息》中对湖区居民性格的一段描述,沈念的个性里也一直有着湖区人豁达和洒脱,“遇到事情我会想得很开阔,顺其自然,不会纠结一些小的利益,得失心不是那么重。”
多年来,从语文老师、记者到作家,沈念的每一种身份都和文字息息相关,也都给他留下了鲜明的职业色彩。
比如,他很关注基础语文教育,也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有时甚至会检讨自己“好为人师”。对自己带的研究生,他不要求学生马上写出好作品,更重视树立他们对写作的正确认知,“走对了路才能走得更远”。
而七年记者经历,让沈念拓宽了视野和心态,学会了和各个层面的人打交道,无形中积累了写作素材,“那时陪着不同领导到东洞庭湖视察,听到了很多故事,它不可能成为我的新闻作品,但成了我的文学。”
“天地间,水流旁,光影里,我始终会看到一个人,与自然万物一起风雨同行、相濡以沫、坚韧生长。那又不仅是一个人,而是前赴后继的一群人。”
《大湖消息》后记中的这个人,就是沈念。“这个时代有很多声音,而我的创作有局限,写科幻题材缺乏脑洞,写都市情感题材缺乏经历,写历史题材还要下笨功夫。”沈念说,“洞庭湖是我的文学原乡,我希望能创作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为它立传。”
文 政协融媒记者 刘敏婕
图 受访者提供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人物》2022年第12期
编辑:邓骄旭


 标准
标准



 A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