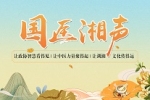当代中医学的伟大成就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理论成就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以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象思维、系统思维和变易思维为主要思维模式,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和精气血津液神等为理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医学理论体系。
20世纪50年代,以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教材的问世为标志,中医学界初步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并提出“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中医学基本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传统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中医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中医理论,如中医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藏象理论研究、中医体质理论研究、病因病机证候理论研究、特色疗法研究、中医原创思维研究等,构建了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体质辨识体系,继承和创新了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与框架,发展了中医病因病机证候理论,阐明了五脏藏象的基本科学内涵,挖掘和规范了中医特色疗法的科学基础,创新和发展了中医理论,为治疗疑难疾病提供了新思路。
中医学对人体体质的认识可追溯至《黄帝内经》,经历代医家不断充实发展,但始终未形成理论体系。王琦构建了中医体质学理论体系,提出了体质过程论、心身构成论、环境制约论、禀赋遗传论四个基本原理,以及体质可分、体病相关、体质可调三个科学问题,建立了中医体质学新的学科分支,构建了人类体质的现代分类系统及标准,揭示了个体体质差异的生命内涵,为中医治未病、慢病防控与共病研究提供了抓手。体质辨识法列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被称为里程碑事件。
络病理论是中医学的独特组成部分。《黄帝内经》奠定络病理论基础、汉代张仲景首创通络方药、清代叶桂丰富发展络病治疗药物是络病发展史的三个里程碑。吴以岭系统构建了络病理论体系,提出“营卫承制调平”等核心观点,并指导临床研发通心络、连花清瘟等系列创新中药,广泛应用于心血管病、外感热病等治疗,显著提升疗效;创立中医络病学,开辟了中西医结合防治微血管病变新领域,取得中医药治疗微血管病变的新突破。
在经络研究方面,相关研究肯定了经络现象的存在,揭示了经络与神经传导的关联,并明晰了相关信号通路。针刺镇痛效果得到了有力的科学论证,针刺镇痛的神经生理学机制、内源性阿片肽及其他中枢神经递质在针刺镇痛中的作用得以阐明。对针灸优势病种效应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推动针灸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转变。经穴效应的特异性、相对性、循经性和关键影响因素得以系统证实,多环节靶向调节的生物学基础得以阐明,经穴特异性理论取得了创新性突破。针灸戒毒帮助成瘾者缓解戒断反应,开辟了新的戒毒途径。
此外,西医学的理论、技术与中医学交叉渗透,有力地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如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包括证候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剂药效化学基础及作用原理研究等;如方法学研究,包括现代中医“四诊”多维信息集成式诊断系统研究、功能性检测在中医诊断中的应用研究、中医临床疗效系统评价体系研究;如现代中医信息的应用研究,包括基于虚拟专用网络技术的中医药研究新模式、中医智能化信息系统研究、中医药古代文献资源数字化研究等。
二、临床成就
当代中医药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尤其在心血管疾病、血液病、急腹症、IgA肾病及疫病防治等领域表现突出。
中医药在心血管病的诊治方面探索出一些有价值的规律。如针对冠心病冠状动脉球囊扩张术和支架植入术后再狭窄这一冠心病防治领域的国际难题,陈可冀对经典名方血府逐瘀汤进行反复深入研究,并研制出芎芍胶囊。研究表明,患者加用中药后冠状动脉再狭窄率明显低于单纯用西药治疗。此外,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清开灵注射液、丹参酮 IIA 磺酸钠注射液、盐酸川芎嗪注射液等多种剂型药物的研制,丰富和完善了中医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手段。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在前维甲酸时代被认为是一种致死性疾病,化疗后完全缓解率仅为30%。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学者先后创制三氧化二砷联合全反式维甲酸双诱导治疗方案,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临床治愈率达到90%以上,使其成为第一种可基本治愈的白血病,并广泛应用于全球。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7医院团队以祛邪扶正为治则,解毒活血、益气生血为治法,研制了中药复方黄黛片口服砷制剂,发现复方黄黛片和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疗效相当。
在急腹症中医药快速干预方面,吴咸中团队强调“通腑泄热、急下存阴”,如大承气汤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可显著降低重症胰腺炎患者肠源性感染风险,缩短住院时间。研究表明,中药灌肠可快速恢复肠道屏障功能,减少多器官衰竭的发生率;针灸联合中药(如四磨汤)可加速腹部手术患者术后肠蠕动恢复,减少粘连性肠梗阻的发生。
陈香美团队在IgA肾病领域取得较大进展,提出“肾络瘀阻”为本病的核心病机,结合病理分级(如Lee分级)制定个体化方案。相关研究表明,黄葵胶囊通过抑制NF-κB通路减轻肾脏炎症,雷公藤多苷调节 Th1/Th2 平衡减少免疫复合物沉积。
中医药除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防治中贡献力量外,在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救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期间,中医药的早期介入有效缩短患者发热时间,减少激素用量。广东省中医院数据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的死亡率较纯西医组降低50%以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防治奠定了基础。自2020年1月起,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中医药治疗纳入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中医药深度介入新冠病毒感染预防、治疗、康复的全过程,与西医优势互补、相互协作,形成了新冠病毒感染防治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中国方案。
三、科学成就
取法古典发明青蒿素,为全球疟疾耐药性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最突出的科学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1972 年成功提取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屠呦呦因其发现的青蒿素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于2011年 9月获得拉斯克奖和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2015年 10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这一奖项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2017年1月9日,屠呦呦获颁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振义、陈竺团队应用全反式维 A 酸(ATRA)和三氧化二砷(ATO)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进行联合靶向治疗,使得这一疾病的五年无病生存率跃升至90%以上,达到基本“治愈”标准。同时,相关团队从分子机制上揭示了 ATRA 和砷剂是如何分别作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致病分子PML/RARα,将白血病细胞诱导分化和凋亡,从而达到疾病治疗的目的。因这一杰出工作成就,陈竺于2016年获美国血液学会(ASH)欧尼斯特·博特勒奖,2018年获得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舍贝里奖;张亭栋、王振义获得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之“生命科学奖”。
中药化学研究有力推动创新药物研发。我国学者通过研究青蒿、天麻、三七、丹参、葛根、川芎、黄芪、当归、人参、五味子、甘草、冬虫夏草、黄精等 200 余种中药,取得了青蒿素及口服双氢青蒿素、斑蝥素、猪苓多糖、靛玉红、川芎嗪、葛根素、山莨菪碱等国际社会公认的中药化学研究成果。目前,我国从中药的有效成分及其衍生物中研制新药200余种,占全国各类创制新药总数的 1/3。
中药资源普查为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保障。自20世纪60~80年代进行的全国中药资源调查表明,我国现有的资源种类已达12807种,其中药用植物 11146种,药用动物1581种,药用矿物80种。2011—2020 年,以黄璐琦为组长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完成全国31个省(区、市)近2800个县的中药资源调查,获取2000多万条调查记录,汇总了1.3万余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和分布等信息,其中有上千种为中国特有种。这些调查基本摸清了我国中药资源的蕴藏量和分布情况,为保护和合理开发中药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分子生药学理论体系推动中药资源创新利用。20世纪90年代,“分子生药学”概念被首次提出。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分子生药学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先后提出了道地药材形成的生物学本质及其三个模式假说、中药分子鉴定的使用原则、珍稀濒危常用中药资源五种保护模式、基于一个系统的“功能基因挖掘—合成途径解析—生物合成生产”的中药活性成分合成生物学研究模式等,推动了中药资源的创新开发利用。
人工麝香研制并实现规模化生产,开创了濒危药材人工替代的先河,为保护珍稀药用资源提供示范。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山东济南中药厂等组成的课题组攻克了天然麝香替代与人工合成技术,研发了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合成濒危动物药材替代品——人工麝香,并实现规模化生产,开创了濒危药材人工替代的先河。“人工麝香研制及其产业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联合企业协同攻关,全面揭示了野生熊胆和引流熊胆粉的成分构成,阐明活性品质比例与药效的关系,创制出濒危动物药材熊胆的高技术代用品——人工熊胆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等运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模拟牛黄形成过程,牛黄体外培育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奖。此外,无性繁殖技术、遗传育种技术、植物生长调节技术等已广泛应用于中药材的引种栽培。
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和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研究对中药现代化影响巨大。张伯礼团队构建了临床准确定位、药效物质整体系统辨析、网络药理学、工艺品质调优和数字化全程质控等核心技术体系,形成了中成药二次开发模式,有力推动了中药产业技术升级。“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高月团队创建了中药早期毒性预测、毒性物质分析和配伍禁忌评价3类技术8种方法,并利用这一综合技术平台对临床易发不良反应的7大类中药的安全性进行了系统研究,阐明了中药配伍理论的现代生物学机制,实证了“十八反”、寒热配伍、甘草“调和诸药”等中医经典理论,“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针刺镇痛的机制研究受到国际科学界高度评价。韩济生团队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发现针刺麻醉镇痛的化学物质基础,即在特定穴位用不同频率的电流刺激模拟针刺,能令脑、脊髓中释放出不同种类的神经肽类物质,从而产生不同的麻醉镇痛效果。
中医基础理论的实验研究向纵深发展。通过动物实验研究“证”,建立了肾虚证、脾虚证等众多动物模型,通过模型认识各证的发生机制及病理、生物生化、免疫等方面的改变。从20世纪60 年代开始,对通里攻下、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扶正固本等治疗方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进入21世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和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医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平台。
中医药循证医学交叉新兴学科促进了中医循证评价研究的发展。1999年起,经王永炎、陈可冀、张伯礼、李幼平、赖世隆等学者倡导推动,循证医学与中医药学从碰撞走向融合。2004年张伯礼组织开展中医药界牵头的第一个中医药大规模循证评价项目,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医药循证医学交叉新兴学科。
四、文化成就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的思想基础和内在精神,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灵魂和根本,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中医学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以人为本、悬壶济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核。当代中医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古籍保护与研究、传统医药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医药科普与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中医药博物馆建设等方面。
系统的古籍整理为中医文化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古籍是中医药文化的载体,保护、整理、研究、挖掘古籍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内容。1983年4月,原卫生部召开会议落实《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将《黄帝内经素问》等11部经典列为首批古籍整理任务,其后又下达第二批200种古籍的整理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国家主导的大规模中医药古籍整理。这批中医古籍文献整理的成果,以“中医古籍整理丛书”的总名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陆续出版。
《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华本草》等文献巨著影响深远。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纂的《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华本草》等大型文献整理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中医方剂大辞典》是明代《普济方》之后又一次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医方集成,收方96592首,2032万字,堪称方书之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中华本草》全书共34卷200余万字,收载药物8980味,绘制插图8534幅,横跨10多个学科,引用古今文献1万余种,内容丰实翔实,项目设置全面,旧识新知兼贯博通,充分揭示了本草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客观地体现了中药学术的完整体系,是一部既系统总结我国几千年本草学成就,又全面反映当代中药学科研水平的传世之作。此外,《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下分《医学分典》《卫生学分典》《药学分典》,是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中医药学类书。
2010年国家公共卫生资金项目“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整理出版“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40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中医药古籍是第一次校注出版,一批孤本、稿本、抄本是首次整理面世。同时,出土古医书的研究、海外中医古籍回归研究成果卓著,引发高度关注。
2012年启动的《中华医藏》编纂出版项目陆续出版。该项目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下组织实施,以“萃取精华、呈现元典”“部次流别、提要钩玄”为宗旨,选择兼具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的重要中医药古籍2289种,分为经典著作、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和民族医药4编,进行系统调研选目、书目提要编纂、数字资源库建设和原书影印出版,是一项多行业、多民族共同承担的全面揭示中医药发展源流、系统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学术建设工程。
中医文化科学普及展现新的态势。2016年2月26日,国务院发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指出推动中医药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将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传统文化、生理卫生课程。王琦、孙光荣主编的《全国中小学中医药文化知识读本》开启了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历史进程。中医药文化主题电视作品《本草中国》《中国中医药大会》等引发社会关注。
传统医药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亮点纷呈。截至目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有传统医药类项目23项,涉及182个申报地区或单位。“中医针灸”“藏医药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和《四部医典》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博物馆体系化建设填补了中医药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空白。国家中医药博物馆于2020年3月正式成立,目标是成为中医药历史文化遗产的典藏高地和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的展示中心,填补了中医药行业尚无国家级博物馆的历史空白。国家文物局2022年度的博物馆备案信息显示,目前全国有中医药类博物馆83家,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1家、二级5家、三级3家。
五、国际化成就
近年来,中医药国际化进程显著加快,在融入世界主流医学体系、国际标准化建设、全球传播及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为促进世界人类健康福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融入世界主流医学体系方面,中国政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理念,积极推动国际传统医药发展。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保持密切合作,中国不仅分享了发展中医药的宝贵经验,更为全球传统医学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2008年,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WHO首届传统医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传统医学北京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将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卫生体系,并指出传统医学的发展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此后,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第62届、67届世界卫生大会两次通过《传统医学决议》,并敦促成员国实施《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年)》。2019年,WHO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外感病、脏腑证等中医病证名称成为国际疾病的“通用语言”。这标志着中医药正式进入世界主流医学体系,更为中医药的全球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权威依据,有力推动了中医药在国际医疗体系中的合法化和规范化进程。
在国际标准化建设方面,中医药走出了一条从点到面、逐步深化的特色发展道路。以针灸国际标准化为先导,相关国际组织先后开展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1981年,WHO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WHO/WPRO)组织成立了针灸命名标准化工作组,开启了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的探索之路。1991年,WHO总部出版发行了《国际针灸命名推荐标准》,WHO/WPRO组织出版了《针灸命名标准》,为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奠定了基础。200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并将秘书处设在上海,标志着中医药国际标准化进入了系统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截至2024年底,ISO已发布117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涵盖中药材、针灸器械、中医药术语等领域。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作为国际性学术组织,依照中医药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及相关需求,积极制定与中医药相关的国际组织标准,为中医药在世界各国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全球传播与推广方面,中医药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发展格局。中国与40 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中医药内容纳入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中药产品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成功注册。目前,中医医疗机构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众多医院均设有针灸、推拿、中医科室或疼痛门诊,每年为数以千万计的各国患者提供优质的中医药服务。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欧盟、非洲、中东欧等地区和组织卫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人文交流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在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方面,“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中医药教育与学术机构开展不同层次、规模的国际合作,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合作开设分校,同时,通过建设“中医孔子学院”“中医中心”等国际合作交流新平台向全球推广中医药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许多中医药院校推出双语或多语课程,20世纪90年代,中医国际教育教材已形成多个系列。新世纪以来,适应海外教学的国际标准化英文版中医教材门类——“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卫生部规划汉英双语教材”“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国际标准化英文版中医教材”等陆续出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等国际组织推动中医药国际教育标准的制定和国际认证,提升了全球中医教育质量。全球范围内,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为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提供了重要平台。
在卫生援外工作中,中医药亦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和优势。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目前,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70多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其中中医药人员约占医务人员总数的10%,成为援外医疗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先后派出400余名中医技术人员,分赴40多个国家开展医疗援助工作。医疗队通过运用中药、针灸、推拿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成功治疗了大量疑难重症,挽救了众多垂危患者的生命,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誉。这些实践不仅彰显了中医药的独特疗效,更深化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何清湖为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医药学院院长,胡宗仁为湖南医药学院中医学院副院长)
编辑:邓骄旭


 标准
标准



 A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