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泉书院 | 看见·最美潇湘

导读:胡氏父子吃饮碧泉,概其神奇,将盘屈石山比诸李愿之乐盘谷。冥冥之中似乎切合了碧泉、隐山的性情。
碧泉书院为南宋的书院,居湘潭县锦石乡碧泉村,归于隐山一脉。其中,有盘屈石山一座,高约100米,清泉暗涌,汩汩不息,曰碧泉潭。
“隐之于山,碧之于泉”,书院由此得名。只是几经毁损,仅剩本亭一座。胡氏父子吃饮碧泉,概其神奇,将盘屈石山比诸李愿之乐盘谷。冥冥之中似乎切合了碧泉、隐山的性情。
(一)
书院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系福建武夷山人,祖脉家山学渊深厚。胡氏父子倡弘洛阳“二程”理学,教化乡里,名噪东南。而洛阳“二程”曾从学濂溪先生,寻根溯源,学源上可归于濂溪一脉。
胡安国生于1074年,字康侯、号青山、谥文定,拜“二程”弟子杨时为师。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胡安国中进士,受举太学博士,多地辗转,职守朝廷史官。其性情耿直,刚正不阿,屡遭排斥,亦屡受提携。
徽宗、钦宗朝,多有升迁之机,其辞而不就。双帝被掳走,朝廷主战、主和之争不断,宋高宗赵构崇文抑武,心机摇曳。看懂了时事的胡安国,渐失官场之志,专注于著书立传。
宋高宗赵构欣赏其才华,让其编写《春秋传》,其欣然从命,有感于时事紧逼和忧怀暗涌,其借春秋叙事,借古隐今,不拘笔墨,让人读后有酣畅淋漓之感。
1137年,高宗皇帝阅过后,作出了“深得圣人旨”的评价。从此,胡安国所注《春秋》,被誉为千古定评。随后,该书被列为儒生必读课本,纳入科考,此书决定了胡安国的学术影响。次年,胡安国病逝于盘屈石山,皈化于一个“仙鹅孵蛋”的小山坡。
由此看来,《春秋传》极有可能出自碧泉寓所。胡安国笔耕不辍,学识渊博,著述甚丰。除了《春秋传》,还有《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文集》十卷、《宋史》立传等。
胡安国育有三子,分别为胡寅、胡宁、胡宏,其中,胡宏学术造诣最高,其出生于1105年,当时,胡安国在湖北路学事职上,后几经碾转,栖居荆门。宋建炎三年(1129),中原发生战乱,盗匪横行,在早期弟子黎明、杨训恭迎下,胡宏随父亲胡安国来到湘潭碧泉村,胡氏父子喜欢碧泉的澄澈和隐山的清幽。父子二人,择依风水,修明堂,建精舍,曰碧泉书堂,此乃碧泉书院之初始。

(二)
胡安国去世后,胡宏承父业,拓延碧泉书堂,改称碧泉书院,并作“碧泉书院上梁文”以记其事。修缮后的碧泉书院儒风满怀,以院门、讲学厅、文昌居为中轴,两进庭院,前低后高,两厢精舍相牵,内隐开阔,外展庄肃。
有人讲,碧泉书院乃湖湘学派的源起之地,有其道理,在此之前,北宋的周敦颐在永州布庐讲学,开启濂溪一脉,洛阳“二程”为濂溪先生弟子,胡氏承“二程”文脉,讲的皆是理学之为。那时,张栻正处在察识涵养的阶段,濂溪之水,尚未注入麓山门庭。
胡安国去世后,其子胡宏在碧潭上建有本心亭,作《本心亭记》,其中写道:“仰望先君,智之不及至远也,然守遗体,奉遗训,期确然自守,不敢与流俗同没,故作亭源上,名曰,有本。”展示了其内心的孝义。
其秉承“人希探本”的性本论思想。倡修儒理,提出执政之要,以仁为本,思想中不乏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畅怀。强调文人士大夫应通过修炼内心,自敛言行,维护朝堂统治。学理精辟,与朝堂所愿心意相随,备受推崇。
明正统年间,胡安国被追赐从祀文庙。一个武夷山人,举家辗转湖南,开办书院,延展二程理学,为湖湘学派的形成铺奠了基石。一直以来,湖湘学子,视之为明镜,尊其为湖湘学派初创者。
早年,胡安国拜“二程”弟子杨时为师,研究性命之学。杨时乃程颐弟子,世称“龟山先生”,“程门立雪”故事中的主人公。胡宏师从父亲,后以二程理学为基,延展“人希探本”的性本论思想,搭建了涵盖本体论、人性论、理欲论、致知论在内的理学框架,为道南正脉的形成,扎稳了根基。
张栻在南宋的名头,不输朱熹,其探访碧泉,拜胡宏为师,足见胡氏父子在湖湘儒脉中,学位之尊。二人初次见面,胡宏以张栻信佛,学理不合为由,几番婉拒,见识了张栻才华后,又感相见恨晚,胡宏曾当着众人面,夸奖张栻:“圣门有人,吾道幸甚。”
张栻不负师恩,成为其学术思想的推崇者,也是集大成者。其上接濂溪之水,拓延道南正脉,为湖湘书院铸了魂,也铸就了岳麓书院的声威。1161年,胡宏去世,遵其遗嘱,归葬于父亲旁侧,以延孝安。
在碧泉书院弘学之时,胡宏心念朝廷,曾修书秦桧,自荐去岳麓书院当山长,未能遂愿,多年以后,张栻来到麓山脚下,受聘山长一职,算是了却了一桩师父的心愿。然而,张栻儒学缠身,心存敬畏,一直不以山长自居,谦卑之怀,足以启迪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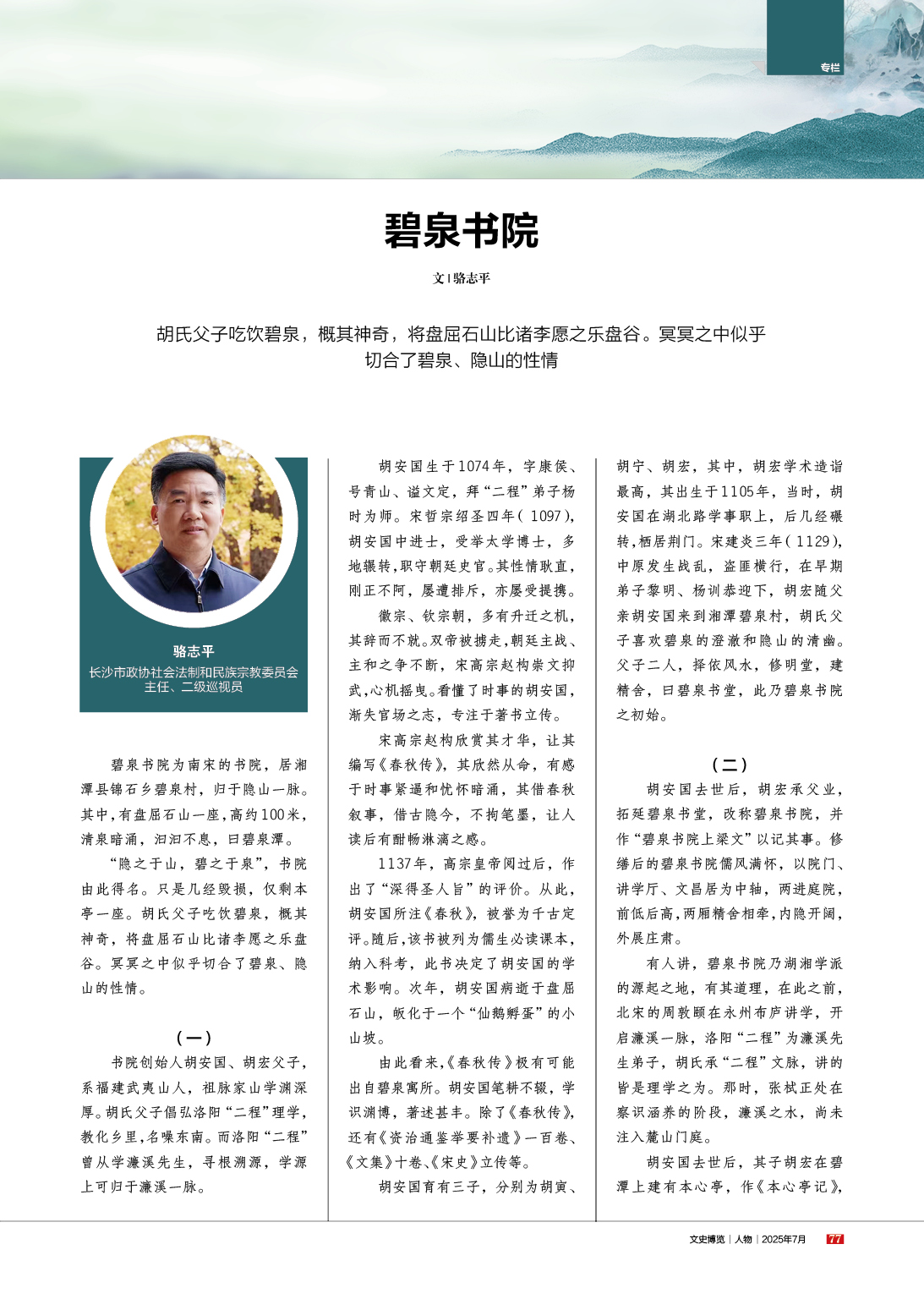
《文史博览·人物》2025年第7期 《碧泉书院》
(三)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七年,门下弟子众多,仅见于《岳麓学案》的就有33人。其开坛论讲,拓展麓山门庭,消除门派之争,梳理湖湘学派,一时车马辐辏,泉池水涸,特别是“朱张会讲”,更是成就了岳麓书院的高怀。至今,朱张渡犹在,浪拍江堤,月系贤儒。
书院文化中的学理之争,早已融汇一体,成为血脉中流淌的记忆。胡氏父子夙愿已了,书院也已归化于尘土之中,唯有碧泉不老,日夜奔涌,相叙无穷的牵挂和流连。
胡宏在本心记中写道:“泉出于盘屈石山之下,凝然清光,微澜无波,潭潭而生。”胡宏将碧泉所倚山石,喻之“盘屈石山”,旨在借唐代处士李愿的“盘谷”阐述自己对“性本论”的理解。李愿认为,“无忧于其心,方为正本之念。”他将士大夫分为两类,一曰建功立业,安享富贵。一曰“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
这种忧乐之怀,“二程”有之,胡宏诠释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了解读。古人之怀,心性为本,秉持法度,心源正觉。
读胡氏父子之书,明湖湘学派之理,能捡拾到不少生命的哲理。过于功利,性不由缰;过于显露,寒湿伤身。等到筋骨已损,长出一身脓包,再刀割火疗,岂不晚哉!
回溯湖湘文脉,胡氏父子辈分不低。书院在宋、元、明、清、民国均有记载,只是称谓不同,有时曰学堂,有时曰精舍,有时曰祠堂。未能见过碧泉书院曾经有过的模样,不过,宋人的风檐,流线通畅,落在隐山碧泉中,自当文趣盎然。
然而,碧泉未老,清澈依然。碧泉之怀,亦未曾注脚。听闻有人出资倡修,实为好事。不过,宋代的书院,风檐绰约,饱含学理,立柱搭梁容易,但要铺设出理学的门阶,讲清湖湘学派的源起,还得下番真功夫。
至少要四周除杂,让亭院相牵于隐山之怀,无有喧嚣,无有挂碍。如此一来,本心亭方可回归本源,碧泉清澈,汩汩而出,方可永不干涸。
文 | 骆志平
编辑:邓骄旭


 标准
标准



 A
A



















